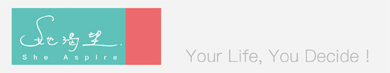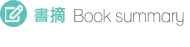隨軍翻譯:一本聯合國維和部隊隨軍翻譯者的文化筆記/ 寶瓶文化
![]()
游在牆上的魚
臘亞醫生是我所執勤醫院裡的醫生,他實在是個有趣的人物,總能在大家感到鬱悶疲倦的時候,適時地講個笑話或當地風土人情給大家醒醒神。第一天見到臘亞醫生,就發現他笑的時候,習慣拉起裹頭巾的尾端半遮著臉笑。大兵們雖然覺得他這個下意識的動作有點女性化,但大致上還是尊重他的,並沒有因此取笑他。然而當地人就沒有如此寬容,好幾次,我看見醫院裡的訪客明目張膽作弄臘亞醫生,他低著頭總是不吭聲不回話。
這一天,來了幾個流氓少年,一看就知道是來鬧事的。這個地區的各個派系之間為了登山證與水源爭執不休,打鬧與爭吵幾乎是家常便飯。生活中出現任何瓜葛,只要在最後抬出這兩個堂皇藉口,衝突馬上就可以變得理直氣壯。
臘亞醫生正好在用午餐,流氓們圍在他桌前,出言不遜地挑釁,不外是調侃臘亞醫生到底是不是個真男人?問他處不處理變性手術?甚至當面就要撩起長布袍的。我在布卡的掩飾下冷眼旁觀,極端厭惡這些無聊的社會渣滓,即使心中再不忿,也只能默默看著臘亞醫生被當眾凌辱。女人,尤其是布卡下的女人,在這封閉的社會裡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臘亞醫生雖然沉著應對,可是看得出來他到底還是有點不安與慌亂。也許,這樣的經驗早就是他成長歲月裡揮之不去的烙印。我們兒時的記憶裡,不都有過這麼一個柔弱而飽受他人欺負的小男生形象嗎?
臘亞醫生是不是同性戀?沒有人有興趣去探問,大夥都有共識,只要不對他人造成傷害,個人的選擇與隱私都應該受到尊重。所以臘亞醫生和我們相處的時候都顯得很自在,雖然有時候他過度女性化的舉止還是會讓人忍不住發笑。在講究男人陽剛勇猛的伊斯蘭世界,如果他的職務不是醫生,他的陰柔想來必不見容於世。
流氓們離開後,臘亞醫生默默收拾好桌子,就消失在簡陋醫院不知哪個角落去了。在我們面前,流氓們不留餘地陷他於窘境,他內心一定極度難過。活在一個假宗教名目實施的極權統治下,人性遭受的打壓與扭曲,那些諸如同性戀、叛教或通姦等莫須有的罪名,讓多少想要活出自我的老百姓們,是被迫以何等卑微的方式在這片貧瘠土地上苟且偷生?
我決定去陪陪臘亞醫生聊聊天,在空置的兒童病房裡找到他後,卻發現他正在牆上作畫。他用紅黃藍綠四色,在蒼白斑駁的牆壁上,畫了一條吐著氣泡的游魚,有趣的是,氣泡並不是一貫的圓形,而是一顆顆血紅色的心。如果塔利班還在執政,描繪或重塑生物形象即等於自比造物主,畫魚的臘亞醫生恐怕要大難臨頭。
臘亞醫生專注地繼續作畫,我靜靜坐在一旁觀看,從畫中窺探他的內心世界。下午的陽光透窗而來,在牆上灑落成一片昏黃的海洋。在群山環繞的偏遠鄉鎮,一個善良的醫生內心正嚮往可以自由泅泳的大海,那裡或許還有美得冒泡的愛情在等待。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和千千萬萬渴望自由與安寧的老百姓一樣,所有夢想也只能化身為一尾游在牆上的魚,在沒有海洋的地方,游魚的軀體永遠固定在戰亂這面冷冷的牆上。
誰來保護你,薩米亞?
薩米亞被嫁掉的那天,她只有七歲。
七歲的薩米亞當然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就算她十七歲,或甚至到了七十七歲,她的命運依舊牢牢掌控在男人手裡,那男人可以是她七歲時的父親,十七歲時的丈夫,或七十七歲時的兒子,這情形頗有點中國《禮儀》「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味道。
而另外一個家庭裡,穆罕默德十歲的小女兒被人姦汙了,而姦汙她的人,是薩米亞的父親。正是父親的罪行,決定了薩米亞的命運。可憐的薩米亞,她不知道在她生長的地方,「公平」兩個字有不一樣的寫法,在父親被捕後,薩米亞一夜之間就成了賠償品,賠給穆罕默德的兒子去訴諸相同罪行,任由蹂躪。不難想像,等待著薩米亞的,將是一輩子可怕的復仇行為。薩米亞無法風光出嫁,她沒有陪嫁的羊或衣裝,也沒有祝福與歡樂,她的出嫁是恥辱性的,背負著父親的罪名。這是阿富汗東北部保守、原教旨盛行,加上千百年來民族習俗超越國家法律的種姓之地。
薩米亞懷抱她無窮的恐懼,被安置到黑暗的地下室,那兒將是她在夫家的棲身之所,她不是媳婦,她是奴隸。兩年多的時間裡,薩米亞飽受這個家庭的糟蹋與虐待,她三餐不繼、飢寒交迫。對她不滿時,有人會扯她頭髮、拳打腳踢,或以燒熱的鐵塊來燙烙衣不蔽體的她,這造成薩米亞體無完膚。冬天的時候,穆罕默德的太太要是想來點娛樂,就會把幾乎光著身體的薩米亞趕到屋外雪地裡,罰她站上數小時,那寒冷一般近於攝氏零度。可憐的小女孩,她大概永遠都無法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要經受如此折磨?
當外界第一次聽見薩米亞的故事,看見她飽受摧殘的弱小身軀時,許多人,尤其是人道主義工作者,都為如此卑劣的懲治方式感到憤怒不已。這個故事牽涉兩個犯罪的成年男子與兩個受害的年幼女童,無辜女童承受了屈辱與懲罰,而兩個男性加害者卻完全不需承擔自身惡行的責任,逍遙法外,只因他們是男性。
什麼樣的習俗,竟可以讓一個清白女孩為自己父親的獸行挨受懲罰?什麼樣的審斷,竟容許把自身的痛苦,報復到無辜的人的身上,而相信這就是公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這樣的吧?
作為一個性侵案受害者的家庭,尤其在一個閨女清譽比什麼都重要的地方,穆罕默德家人的煎熬與憤怒不難理解,如此手段,就算放在文明社會,大概也會有不少性侵案的受害家庭為之叫好吧?女性身體受辱的創傷可是一生一世的烙印。然而合理、公平兼具人性的賞罰制度,難道不就在於不把自身經受過的痛楚,莫名加諸於不曾犯錯的第三者身上?尤其那還是一個只有七歲的小女生?
我不知道薩米亞的父親心裡痛不痛?自己的女兒如此被人蹂躪,或者真的讓他明白了受害者父親的感受而悔不當初。可是,任誰都要這樣問問:如果你是一個好父親,如果你真的心懷愧疚,那麼,你是不是早該捨身救女,誓死不從?在天天鼓吹你男性比女性優越的地方,你是不是早該有所擔當,不讓你的七歲女兒——一個女性,代你去活受罪?你這還算是個男人嗎?
薩米亞,人人都為你流淚,都希望可以把好不容易解救出來的你緊緊擁在懷裡,給你呵護,給你憐愛,給你從七歲起就失去的童年歡笑。然而這是阿富汗,許許多多的女性,許許多多的薩米亞,她們都如你一般,在男權淫威下被強暴,被潑硫酸,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被布製的牢籠所囚禁,被販賣,被折磨,被摧殘。如果有誰膽敢反抗,還會被切掉耳朵、割掉鼻子、鋸掉乳房。她們無助的眼神跟你一樣,看不見人生美好的遠景與希望。在一個假神權、父權制度名正言順欺凌女性的國家,以宗教為蔭庇的陋習會加害於你,連本應該保護你的父親,都要你為他承擔罪行。在這樣一個讓人充滿無力感的地方,誰來保護你,薩米亞?它是如此叫人心碎。
幸福的糖果
像養在深閨裡的姑娘般,人數稀少的女翻譯被軍隊圈養在基地這個深閨裡,輕易出不得大門半步。
稍具風險的任務都分派給男翻譯去負責了,閨女們天天在營地裡巴望,巴望出門回來的哥兒們,給大家講講外面世界的精彩故事。男翻譯或者男兵們,也很喜歡被閨女們纏著要聽故事的那種英雄感,他們侃呀侃地——螞蟻小兵通過翻譯和沙漠蛇蠍談判;碩大的駱駝蜘蛛愛上了夏威夷大兵,把自己辛苦織出來的互聯網讓給那哥兒無線上。女生們聽得一愣一愣地,皆大歡喜。
這一天,被太陽曬得垂頭喪氣的我,在營地路上被人叫住,抬頭一看,是自己排裡的班長迪奇和約瑟。擁有三個小孩的迪奇看見我這毫無鬥志的樣子,就從軍包裡掏出一把花花綠綠的糖果要送給我吃,我婉拒後約瑟就說話了:「怎麼給你糖果你也不要?有糖果吃是很快樂的事啊!」
我看著他們,不斷搖頭,我的胃有點毛病,一向不能多吃甜食。為了應付軍旅生活的體能所需,軍隊供應的食物大多高熱量,我已經被甜食弄得腸胃極不舒服。可是不管什麼理由也罷,拒絕甜食一般都會被牽扯到「你是不是在減肥」這話題上,我只好勉為其難地解釋:「天氣那麼熱,糖果甜膩膩的實在叫人受不了。」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糖果吃還想減肥。伊拉克的小女孩,作夢都只夢見糖果,可是糖果偏偏不易得。」約瑟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
「我知道我知道。」我拚命點頭,饒了我吧哥兒們!天氣這麼熱,你們卻來跟我談糖果跟幸福的指數。我掙扎著想,要不乾脆接過糖果算了?可是為時已晚,「哥哥講故事症候群」發作,約瑟開始給閨女講故事,外面世界精彩的故事……
「我們到鄉下巡邏的時候,偶爾從裝甲車上撒糖果,天女散花似的,小朋友們都搶得不亦樂乎,簡直就是一場糖果嘉年華,沒有人會拒絕的。我們撒呀撒地,撒得很快樂,感覺自己完全是個聖誕老人呢!」約瑟說得眉飛色舞,我聽著,卻實在不忍心去提醒他,聖誕老人不會開坦克去派糖果,聖誕老人身上不帶槍。
「那些小孩,男的女的,衣衫襤褸,鞋子破舊,看著實在可憐,唉!」迪奇歎息著說,「後來我們出去巡邏,都成了規矩了,一大包一大包地帶著糖果及飲料去分派。」
說話的迪奇語氣有點不自覺的溫柔,他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小孩。在這個時候,聽故事往往就變成給大兵們心理治療,因為翻譯是「外人」,他們比較願意對翻譯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勝過去向軍中牧師傾訴。我於是告訴自己要平心靜氣去聆聽,要隨著大兵關心的話題去嘗試了解他們的心情。
「小女生還可以在外面亂跑啊?」我說,「小時候我媽媽只會嘮叨『不可以吃陌生人的糖果!』。」
「哎呀!那些小女生才真正可憐喲!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臨空就撒一堆糖果,撒完一看,搶拾到糖果的清一色都是男生,小女生在後面怯生生地,什麼也沒有得到,也不敢跟男生們去搶。」約瑟說。
「那些哥兒也真沒意思,難道不會得了糖果後再分給自己姐姐或妹妹吃嗎?」說完我馬上就察覺自己是白痴一個,伊拉克男性是如何對待女性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也許,我內心還在隱約期待一個奇蹟,那些像白紙一般的幼小心靈,或者還未被性別歧視的觀念所汙染,還保持著對自己手足毫無條件的寵愛?
「哈!」約瑟果然對我翻白眼,他臉露不屑:「他們搶到糖果馬上就塞到自己嘴裡了,還會考慮到自己姐妹?」
「後來知道了,我們派糖果就只派給小女生,男的一個也不給。」迪奇說。
我正要拍手叫好,正想開口罵「活該那些臭男生」時,約瑟卻突然激動起來,他語氣急躁地數落:「派完糖果,我們車子才開沒幾呎遠,就發現那些臭男生在揍那些小女生,搶走她們手上的糖果,那些狗爹養的,年紀小小就已經學會欺負女生了啊?!」
我聽到這裡,也不禁跟著氣憤地詛咒:「果真是狗爹養的啊!」那些挨揍的小女生,實在太令人為她們感到心疼,還那麼小的年紀,就已開始被男性沙豬所欺凌,在如此環境下成長,她們被扭曲的心靈就會以為男人打女人是理所當然的,怪不得我所認識的阿拉伯女性總是對家庭暴力逆來順受。
「不過後來我們就有了對策,分派糖果的時候,把男生都趕開,把小女生都圈在車子周圍,給她們糖果、餅乾、巧克力,給她們冰鎮飲料,叫她們馬上吃馬上喝,吃完喝完才可以離開,可是有些小姐姐居然還捨不得自己享用,說要留著帶回去給哥哥或弟弟。」
「唉!女生與生俱來的母性,是不管在任何惡劣環境裡,都想著要把他人照顧好的。」我感歎。看著約瑟與迪奇這兩個大兵,心中掠過一丁點感動,我沒有對他們說出口的是,他們心裡還真有個柔軟的角落啊!我想像一個美麗的世界,在那裡,兵哥哥寵愛小弟弟,小弟弟寵愛小姐姐,幸福的糖果在每個人手裡爭相傳遞。
「這些小女孩,就只有這短暫的時間可以享受一點點寵愛,也只能有這個機會讓我們大兵疼愛疼愛。她們長大後,等待著她們的世界將會艱苦無比,到時只能自己疼自己了。伊拉克這地方,男人哪裡知道女人是用來疼的呢?!」迪奇說。
我認真地看了一下迪奇,輕輕笑了起來,他可真是個世紀好男人喲!如果他還沒結婚,單憑這句話就會有很多女人願意嫁給他的,懂得女人是拿來疼的男人畢竟不多見。
我伸出雙手把迪奇的糖果接過來,像接過一掌心的幸福,幸好我不成長在沒人疼的伊拉克。
路上一輛悍馬車歪歪斜斜地開過,約瑟與迪奇瞪了一眼,吐口痰後不約而同輕蔑地說:「早就猜到是個女的在開!」
我看著面前這兩個男人,不禁重重歎了一口氣!感到太陽突然就又熱起來,我也從幸福的雲端摔落地。通過比較才能感受到的幸福,並不是真正的幸福。把糖果又還給迪奇,我沒好氣地乾脆搪塞:「你知道女人總是善變的,所以你們的糖果我還是不要了。我在減肥,而減肥讓我感到幸福。」
![]()
作者介紹-禤素萊
* 出生於馬來西亞有「古城」之稱的馬六甲,成長在遺跡遍佈的環境,聆聽歷史風雲,自幼深信馬六甲河就是遠航故事的開始。東、西文化一度以超過八十幾種語言在這河畔熙攘交流,關於 Lingua Franca 此起彼落的遐想,潛移默化了作者自小就對語言學習的興趣。
*留學日本、德國,並曾在台灣淡水短暫逗留。旅居海外二十幾年後,在其心目中,出生地大馬是英文所指的「母國」Motherland,長居地德國是德文所指的「父國」 Vaterland, 兩種指稱皆意中文的「家國」,馬來文形容的「水土」Tanahair。有父有母,理所當然,自認因此不存在雙重認同的矛盾。
*2007年始,任職隨軍翻譯,為聯合國特遣北約維和部隊服務,專職提供軍隊語言、文化上的訓練。因此機緣,得以近身觀察戰爭機制、族群衝突與殺戮,並體驗封閉社會各種匪夷所思的文化衝擊。
*國際筆會屬下美國筆會會員,參與世界各地流亡、獄中作家等人權事項。
*目前居住美國因著飛碟傳奇而名聞遐邇的羅斯威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