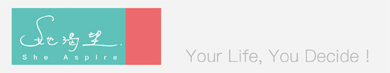香港雨傘革命訪問-我們戰的都是體制/ Sandra
封面圖片:photo credit: pasuay @ incendo via photopin cc
佔中這段時間,一個人帶著相機在金鐘與旺角遊走,在多個佔領區徘徊,聽聲音,但其實不只是聲音,對我來說像是喧囂,像是吶喊,民眾在你面前,有些念書、有些坐著、有些運送物資、有些躺在帳棚裡睡著了……,這裡是金鐘夏慤道,貼滿標語和雨傘;當然過了幾個地鐵站來到旺角,偌大的彌敦道佈滿帳篷,香港朋友帶我經過這裡,口中說著十幾年從沒能走在彌敦道上(是九龍區一條連接旺角與尖砂咀的主要幹道),又是另一個混亂與靜坐的示威區,廣播與小型公民講堂在我耳邊跑,還有遊客一齊拼湊這幾日,每夜每夜的旺角。
這幾天試著與占領者對話,試圖從幾萬來來去去的人當中,尋藉著幾位受訪者來理出幾段脈絡。香港人,你們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而來?這幾個基本問題,有太多疑惑等著去解答,有太多故事可以傾聽。我想找不同身分的佔中人士來聽聽他們的聲音,聽現場的狀況,最主要的,佔中雖最開始是由學生罷課一觸即發,隨後轉為學生運動,更擴散到全民運動。
中六學生阿Bee,我在對抗這個體制
我在物資站前看到阿Bee,她坐在物資站前的椅子,看起來顯得有些疲憊,招呼和幫忙來拿物資的集會民眾,她說來到這裡大約十幾天了,自從警方發放第一枚催淚彈以後,「我家人挺支持我的,他們覺得有些事一定要發聲,如果現在不發聲,以後就沒有機會」,她第一天是跟爸爸來的,後來就是自己來這裡物資站幫忙,「我自己留下來的,因為我覺得這個普選是我們這一代的未來,2017年我可以投票的時候,我不想我連這個選擇的權利都沒有」,而現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就是1200人選出來的,「我們覺得這個不是真的普選,那我們在爭取一個全香港人有機會投票的一個人」,問題是中國不讓香港,中國想先選幾個人給香港,再讓香港人去投票選出,「這個就不是人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我就上街,我對抗這個體制。」

半工讀吳同學,自製舉牌,追求民主,期望他人了解
半工讀的吳同學,戴著口罩,舉著手中的標語,現正就讀副學士(香港特殊的文憑過程),他表示:「我第一天來是因為警方發放tear gas後一天來的,我守在銅鑼灣,我看到新聞,警方跟黑社會混在一起,我開始有點害怕的感覺,我來到金鐘,上個星期放假的假期比較多,我罷工了一天,我的時間比較充裕,因為每天還要上班,我放工和lunch hour我都會下來支持,星期六放假也來了。」吳同學說,第一天在銅鑼灣真的很感動,陽光從Sogo大樓直射下來,當天真的很熱,沒有帳篷,只有三盒退熱貼,台上的人不斷呼籲麻煩你們的朋友送退熱貼過來,不到15分鐘,已經有4大袋,「就是很團結,我看到的是不斷有物資送過來,水、麵包餅乾,我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集會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民主,我感受滿多的,我對政治沒有很了解,我想主動了解這個社會和政府怎麼在運作。」不是坐在這裡聊天,目光比他人更多了一份堅定感,「第二天我就自己來了,沒有跟朋友」,他的眼光總是清明,不看著我,望向遠方,像是思索像是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手中握著自製的舉牌,「有人在說這裡已經是一個小社會,多反省一些,如果我在這個小社會,我就是一個工作者,我來工作、支持、安守自己的崗位。我知道我出的力不比其他人多,但是我希望透過這些很短的slogan,喚醒一些人。你知道香港的電台不像台灣那麼多,香港只有兩個,兩個都是給政府控制的。很多不了解事情的人就是看這兩間新聞,所以我覺得真的很難過。」我想起要採訪他時,他還謹慎地問我是哪一間傳媒,怕會有不利的報導。「有很多傳媒來訪問我,我希望過這些機會讓不瞭解香港狀況的人了解。用我的行動來改變他們的想法。」

大學生彬哥,想要真正的普選
夜晚旺角現場較混亂,還有警察在旁,彬哥,全身裝備著防護衣,現讀香港教育學院。在旺角和金鐘兩邊跑,相較之下,金鐘的人比較有文化、團結、自律的,「他們是會互相幫助的,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他們會馬上來看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助,像是有一天我們在特首辦外的夏慤道睡覺,那天很多人已經睡了,但突然來了一幫警察,來到前線佈防,其他人會馬上來叫醒你、跟你說加油。」
夜晚有風,時時會被冷醒,他與朋友睡在馬路上,沒有被袋,一種最簡便的占領姿態。「我是在旺角第一天佔領有去,在街上聽到很多人大叫、四處有人打架,很吵,很多人都在幫忙布置場地,有很多的『MK仔』(Mongkog旺角,旺角的人、流氓,一些比較潮流、前端,有諸多意思,偏負面)來幫忙,把物資從這裡移動到下一個物資站。」他們在那邊守著,遇到旺角很混亂的情況,一個很恐怖的地方。「有很多的黑社會在那邊,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去對警察做一些他們平時不會做的事情,圍著警察,但是比較好一點,有一些人是保護警察的,因為我們運動的名義就是和平理性的,所以我們也會去保護那些警察,黑社會包圍警察、而佔中人士在黑社會之內包著警察、保護警察,形成三個圈。那時候我在很遠的地方看著他們,看見了警察在前面走,後面有很多黑社會拿東西砸警察,在這之間就有很多的集會者跑過來保護警察,黑社會就走了。」
說起當初本來是罷課不霸學也想過自己會出來,一直以來也是想要真正的普選,但覺得無論如何做什麼事情好像都沒有用,在這個機會激發了自己站出來。「我想要真普選,但激發我出來的是警察捕捉黃之鋒。黃之鋒(最近剛滿18歲,學民思潮召集人)在26號給警察抓了,我就通霄出去了,來了10幾天,都是晚上,在金鐘或旺角。」
彬哥說起佔中的主因,「你應該對學生體諒,他們還是學生啊,就像我也是學生,他們還是小孩,18歲都還不到,你竟然這樣子對那些中學生,還有胡椒噴霧,真的太過分,所以就出來了。」他表示,想要真正的普選,基本法說要有普選,怎樣去實行沒有說清楚,所以說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爭吵就是因為沒有說清楚,中國有中國的說法,香港有香港的說法。「我的訴求就是不要中國的那種,要是我們香港人自己提名的候選人,我想要的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來選的,一般的公民也可以出來選。現在那些出來選的都是中國自己選的,這一些人組成全部都是中國那邊的。我想要的不是這樣的選擇。這個普選影響了整個香港。」
還有一點,佔中更像是場世代之戰,「香港是給那些大人、老人去控制整個體制和社會,現在的佔中很大程度像是一個世代的對抗,老人和年輕一代的對抗,既得利益者和被剝削著的對抗。」

測量師莫紹文,絕食爭取群眾覺醒
莫紹文,一個人坐在自備的小板凳上,我觀察他許久,在集會現場時時有不同的人前來聊天、或拍照,他敘述自己的抗爭的經歷。身為前國家測量師(surveyor),與特首梁振英就讀一樣的專業,現在卻在一場運動的兩端,小人物、大體制。「我跟所有的團體都沒什麼關係,我是個人的,為什麼跑這麼前面,還絕食,就是因為政府發催淚彈。」他娓娓道來,當天在上班,晚上就出來,「我希望用我的身體去要求警方不要再放催淚彈傷害小孩,我當天,身上什麼防護都沒有,因為我希望他看見我是一個人,看見我的眼,對著我的眼來打。」後來警察不打了,他說,這個舉動可以讓對方承受很多心理後果,想起從前打過一個投降的人。如果什麼都保護了,對方看不見是一個人、看到的是一個物件,就項練靶一樣,沒有同理心。「我豁出來,以為自己很安全,他還發了3個催淚彈給我,我很憤怒,就上前跟他說,『你為什麼不抓我,我投降了,你還打了我』,警方朝著我往後退,我不停地叫,『你為什麼不抓我,你叫你的老大出來。』堅持30分鐘後,莫紹文回到安靜的地方,因為他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必須休息。
「回頭想,這個運動目標是爭取普選,爭取後的目標是可憐我們之後給我們的,不如現在爭取到萬人都被他蒙騙的民眾,爭取普選是最後的結果,但如果中間沒有群眾的覺醒,什麼都不是,我就去絕食」,因為awakening必須要有一些犧牲,「我想以中產階級這個身分站出來,我絕食,應該是倒下來的,讓政府看見一個中產的人為了飢餓倒下來。」
為什麼要強調中產身分?不單只是草根的人們,草根有些時候是因為太忙了,為生活忙,他覺得很煩,就不聞不問。但中產呢?他們其實有時間的,但是覺得生活挺好的,那為什麼要放棄現在的體制呢?將來他覺得這樣可以賺錢,拿到一點的社會地位,所以他們還是反對佔中的,他們覺得現在的普選方案是政府給的,他們覺得沒問題的。「中產階級可以看看,現在年輕人這麼長時間卻工作沒有好的回報,這都是體制的問題。不單是他不念書、沒有好的懷抱,他運氣不好,而是有一個不公義的體制在管制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可以工作、讀很多書、工作很勤奮,但他沒法開創自己的道路和未來,連買房都沒可能、在公司內部提升都沒可能。「特別是特權階級從上面來,已經安插了人進去了,比你年輕、比你學歷低,他是傳二代,你怎麼辦?」現在的中產呢,自己的成功不是下一代可以重複的,如果你現在不站出來爭取,你的兒女會恨你一世的,「我不一定要爭取好的普選制度,我爭取的是全民的覺醒,我站出來對抗這個體制。」

佔中不止是佔中,更多的是背後的焦慮、問題、社會結構,旺角和金鐘,物資的溫情,隱匿於高樓大廈中,更多的是有許多努力,許多對抗,香港,不只是四個人,一場運動可以有多少聲音,已經一個月了,運動該何去何從?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力量。
  |
 Margaret 專欄|職業婦女生的各種習題part 2
Margaret 專欄|職業婦女生的各種習題part 2同我一樣,是全職婦女的妳—我們,以家庭為重,孩子更當然是牽掛在心頭,但同時,我們努力達成工作目標,期盼著更亮眼的成績,也要維繫著與同事間的團隊互動。
 JC.CHOW 專欄 | 閱讀2017 , 為翻開2018作準備
JC.CHOW 專欄 | 閱讀2017 , 為翻開2018作準備十年人事幾番新... 用來形容這十年的轉變,真的再貼切不過了。2016年,我認識了不同的新朋友,也認識了一位重要他人,為2017年打開了充實溫暖也更內省的一年...
 照顧別人前先照顧好自己
照顧別人前先照顧好自己就像搭飛機時的安全守則一樣,在幫孩童戴上氧氣面罩之前,要先幫自己戴上。我相信一個快樂的老婆、媽媽才會有一個快樂的家,所以從現在開始努力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不想要的是什麼,並且去爭取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