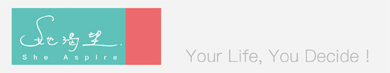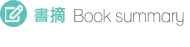黃淑文-我的旅程:給自己癒合的機會/ 方智出版社
![]()
〈前言〉
我的旅程:給自己癒合的機會
生命難免有傷痕,每個人的身上,多少都帶著一點傷。
這個傷,可能是身體的病痛,或心理的創傷。
我們常在創傷中迷失自己,否定自己,讓自己完全變了樣。
我們常誤以為不會好,於是就放著讓它痛,對自己的傷視而不見。其實只要找對方法,加一點探索的勇氣,傷口是有可能癒合的。
前提是,你必須給自己癒合的機會。
三十年的皮膚過敏,意外得到改善
從十歲開始,只要一流汗,或太過悶熱,我的皮膚就會過敏,發作起來奇癢難耐、痛苦不堪。一開始,經過醫生檢查是汗斑,後來伴隨皮膚過敏引起局部紅疹,反覆發作抓傷便在我的身體留下各種疤痕。
這些斑點和疤痕很醜,我常用衣服遮掩,其實是想逃避童年去工廠當童工,染上皮膚炎痛苦的記憶。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我越不敢正視它,它就變成無法碰觸的疙瘩,不管穿衣服、照鏡子,我常漠視它的存在。很多醫生坦言,像這樣的汗斑加上皮膚炎實在很難根治。既然不會好,發起病來,就算忍不住抓癢抓到流血,自己對自己生氣,癢起來也只能放任讓它癢,不知不覺竟然就過了三十年。
直到有一次,過敏性皮膚炎又發作了,我癢到受不了,突然動念解開衣服的鈕扣,狠狠的把身上的幾處疤痕和斑點看清楚。
我照著鏡子,第一次定定的看著這些斑點。它們那麼醜,卻真實的留在我的身體裡,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很多痛苦,你不想讓它發生,但它還是發生了,還狠狠的在你心上留下痕跡,怎麼樣也抹不掉。為什麼我不能接納它的存在,和它對話呢?
奧修曾說:「靜心(meditation)和醫藥(medicine)來自同一個字根。醫藥,意味著可以治療身體的;靜心,意味著可以治療心靈的,這兩者都是治療的力量。小心你的創傷,不要讓它滋長,要讓它被治癒。唯有當你走到傷痛的根部,它才能夠被治癒。」
「唯有當你走到傷痛的根部,它才能夠被治癒。」這句話重重撞擊我的心坎,如果現在的汗斑是過去到工廠當童工造成的,只要我能夠回到根源,療癒當年的創傷,當年的傷口好了,現在的汗斑也許就會消失。
回到受傷的那一刻,把情緒發洩出來
我透過靜心,走入童年,第一次勇敢的掀開記憶,跟去工廠當童工感染皮膚炎、才十幾歲的我—因為汗水黏上工廠白色粉末和骯髒的灰塵,導致全身皮膚過敏不知所措,卻仍然賣力工作的小女孩—說對不起,安慰她,請她原諒我。
我忍不住失聲痛哭,淚水沿著臉頰滑到脖子和胸口上的汗斑,好像啟動了什麼按鈕,長期搔癢、搞不清楚來源的焦慮和疼痛,一下子全部湧上來襲捲了我的眼。我告訴自己,想哭就哭,把三十年來沒哭的眼淚,全部痛痛快快的哭出來。
不知哭了多久,我突然覺得應該送給在工廠辛苦工作的小女孩一個小禮物。
想起小時候,非常喜歡樹上翠綠的小果子,於是我爬上家裡的柚子樹,祈請柚子樹送我一個鮮綠的果實,然後放在胸口,冥想當年的小女孩收到翠綠果實開心的模樣,那種感覺好神奇。現在的我和過去的小女孩是一起連動的,當現在的我願意接納過去,傳送美好的能量給過去的小女孩,受傷的記憶在當下馬上得到修復撫慰。
我持續把目光停在內在的小女孩做觀想,記憶的閘門打開了,像洩洪一般,跑出一個又一個畫面,有些記憶是美好的,但有些記憶是我再也不願意探看的。我很想逃,卻被什麼狠狠抓住了。是那個小女孩一把抓住了我。
「你怎麼可以那麼狠心,再度把那個最脆弱最需要呵護的小女孩拋棄?為什麼不聽聽她要跟你說什麼呢?」
一旦走進記憶深處,和自己相遇了,很多聲音在心裡打架。我回過頭,淚眼汪汪看著小女孩。驀然間,我看到小女孩在醫院檢查汗斑,醫生露出驚訝、鄙笑的表情深深傷害了她。原來最受傷的記憶,不是當童工的辛苦,而是在醫院檢查受到醫生的奚落和鄙棄。
「醫生怎麼可以這樣?」現在的我真想一拳揮過去,想像當時有人在旁邊保護我,木訥的爸爸應該要開口制止,但他沒有。爸爸只關心我的病情卻未照顧我的心情,爸爸不懂也不知如何處理當時的尷尬,他完全被自己的擔憂綁架了,任由醫生的奚落、鄙視像亂箭一樣射穿我的心。
重新看見這一幕,我摀著胸口又惱又氣,打開日記簿,像被烈火燙到的猛獸失控亂吼,在紙上亂塗亂畫。我把醫生畫出來,把它揉成一團撕個粉碎,直到我冷靜下來,聽到內在有個聲音告訴我,小女孩最需要的是修復,而不是報復。
重設新的生命劇本
我重新打開記憶的帷幕,問那個受傷的小女孩需要什麼?我想像當時在醫院,不是只有木訥的爸爸陪同,還有溫柔的姊姊在現場。體貼有正義感的姊姊,一定會斥責醫生,馬上帶我離開醫院。儘管當年姊姊不在現場,但這樣的觀想撫慰了我的心。(或許當年回家後,應該把自己的憤怒、難堪全部告訴姊姊才對。)
記憶像個連環炮,一旦點燃了,就一個個炸開,就算你措手不及也無可奈何。是我自己,再也不願拋棄自己了。我睜大眼睛,把當年的我,到底經歷了什麼事,一件一件看清楚。原來,病痛都是連串的傷痕堆疊而成的。就像很久沒有整理的抽屜,我們只往裡面塞,不願意整理,也不願意觀看,有一天塞滿了,無法隱藏了,不去整理都不行。
就這樣,我面對了童年的事件,看見染上汗斑的辛苦女孩、被醫生鄙笑的憤怒女孩,同時也看見當年講話口吃的自卑女孩,還有煩惱手毛和腳毛太長被同學嘲笑的受傷女孩……我走入時空隧道,一次次的撫慰她們(和當年的自己對話)。我知道,過去的小女孩和現在的我住在同一個軀殼裡,唯有過去的我和現在的我願意在同一個身軀裡對話,才能彼此撫慰、彼此修復。
想像自己完全癒合的樣子
循著記憶的軌道,我深入了童年的記憶,聽見年少的自己說了六個故事,每聽一個故事就爬上家裡的柚子樹摘下一個翠綠的果實,送給童年的自己。想像這六顆果實吸收當年小女孩的痛苦,幫助小女孩長出自己的嫩芽,重新長大。
最後,我觀想一道柔和的光,暖暖的照著小女孩的皮膚,承諾給她愛,給她祝福,想像小女孩重新擁有完美漂亮的皮膚,開開心心、完全癒合的樣子。忽然間,童年受創的畫面,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刪除了,我看見小女孩身上的汗斑傷痕全部消失,旁邊還圍繞著可愛的小天使,送她許多翠綠的小種子,一顆一顆的發芽,開出翠綠的嫩葉和漂亮的花朵。
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貫穿我整個身體,讓我不由自主的在家裡佛堂跪了下來。我曾經恨過父母,不諒解他們送我到工廠做假日童工,讓我染上過敏性皮膚炎痛苦三十年。但當我感覺受傷的小女孩開始復原,領受強大的療癒能量時,我突然好想跟上蒼說謝謝。
從嚴重受創,到想像自己完全康復、平靜釋懷,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幸福,或許那是一種我終於懂得如何愛自己的幸福。哇!我終於從三十年的痛苦解脫了。在那個當下,我第一個想到的竟是我的父母,我想要跟父母說,我不恨他們了。
「感謝父母生下我」,一種重生,想要重新長出自己的決心,一股強大的力量,像扎根一般穩穩的安住了我。對我來說,所謂的療癒,就是改變生命中的「視覺畫面」,用正面光亮的影像取代負面陰暗的記憶。
那六顆從樹上摘下來的柚子,或許吸收了童年負面的痛苦,過了不久就全部腐爛了。我對它們說了謝謝,埋在柚子樹下。奇妙的是,經過那天的自我傾聽、自我療癒,幾個星期後,我身上的汗斑漸漸消退,累積多年的傷痕斑點也漸漸消失,一直到現在都未再發作。
我想我變勇敢了,就算汗斑再發作,我也不怕了。我突然對自己產生一種信心,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會被擊倒。不是我很厲害,或自以為不會遇到挫折和病痛,而是我終於學會愛自己,愛自己的軟弱,也愛自己的眼淚,愛自己所有的一切。
最大的療癒能量,在自己身上
《前世今生》作者魏斯博士曾說,療癒發生在許多層次,生理只是其一,真正的療癒必須發生在心靈層次。如果沒有找到負面的模式並加以破除,同樣的傷害、失去、病痛或挫敗,可能會在今生或不同的來生反覆出現,直到我們學到該學的課題為止。
每一個靈魂來世間,都會在出生前擬定學習的功課,有的人來人間學習寬恕,有的人學習信任。不管我們今生擬定的課題是什麼,所有的傷痕和失去,都只是為了讓自己的靈魂成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承受的每一個痛苦、每一道傷痕,都是我們的靈魂出生前,為自己量身打造的。通過傷痕的考驗,學到我們該學的,完成自己的功課,痛苦自然就消失,因為痛苦和傷痕是對應我們學習的課題才會存在。痛苦就像在學校修學分,通過測試,及格了,就不必反覆重考重修。
表面上,我療癒了困擾三十年的汗斑,實際上,真正讓我解脫的是,我走出了引發汗斑背後種種的創傷。汗斑和童年的傷痕,只是為了讓我學習「愛自己」才會存在。一旦我學會如何愛自己,便自然終止汗斑對我的折磨,就算汗斑再度發作,我也知道如何與它對話,從中學習,而不再像以前隱忍、壓抑,讓自己平白受苦。
或許我們無法避免身體的病痛,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因為心靈的正能量,降低身體病痛對我們負面的影響。
![]()
作者簡介-黃淑文
心靈繪畫師、認證園藝治療師、YAI國際靜心引導師,色彩諮詢師,部落客百傑「文學創藝類」金牌獎得主。因為保留20年前學生所畫的漫畫(櫻木花道),因緣際會發願終身擔任受刑人的老師。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畢業,任職國中教師7年,被形容為「叛逆學生最愛的老師」,作品獲台灣創造思考教學優異獎。因為養育兩個孩子,將生命歸零重新活過,2005年辭去教職,成為專職作家。有人說,讀淑文的書,就如她牽著我們的手,和她一起走過生命的巡禮。淑文的文字,就如她的人,質樸溫暖,真誠坦白。
著有《在愛裡活著》、《媽媽做自己,孩子就能做自己》、《最長的辭職信》、雲門流浪者計畫《趁著年輕去流浪》、《骷顱與金鎖:魏海敏的戲與人生》、《媽媽的讀心術》。其中《最長的辭職信》的文章《從浪子到鐵人》,以及《趁著年輕去流浪》多篇採訪流浪者文稿被編入大學國文教科書,作為生命教育與自我探索的讀本。
作品集結於桂花樹網誌和康健雜誌(名家觀點)網站,目前是《康健雜誌》《媽咪寶貝》專欄作家,並在學校社區開設靜心引導課程和親子彩繪課,透過靜心和色彩幫助父母和孩子觸摸彼此的心。
【相關連結】
1.黃淑文(桂花樹)網誌 一位熱愛生命的心靈作家
2.康健雜誌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