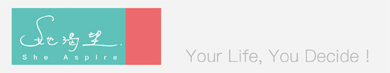開場/ 余秀芷sleeve
1998年,我人生中的分水嶺,沒有想到過這分水嶺會那麼快就來臨,在我20出頭歲的時候,我從非障礙者,成為了障礙者,「癱瘓」讓我被迫重新去熟悉這個身體,熟悉這個曾經熟悉的世界。
這世界變得有點矛盾,許多人跟我說:「你依然是你,坐在輪椅上也沒什麼不一樣。」但另一方面的這環境,卻處處讓我挫折的感受到我跟大家、跟過去的自己很不一樣,即使大家用很常見的勵志小語來鼓勵我,「要學會跨越障礙,克服困境」,但在階梯面前,我的輪椅如果硬要跨越障礙,就面臨翻輪椅的命運,然而在坐上輪椅成為障礙者之後,這社會看待我的眼光也開始有了些微妙的變化,人們對我投以悲憐的眼神,而無論我做任何再平凡不過的事情,也被以勵志的角度來解讀,有那麼些時候,我被搞得精神緊繃,直想把自己給藏起來。
我的確將自己藏起來過一陣子,大約有兩年的時間,我發現出門是那麼樣的不容易,只因為我坐在輪椅上,餐廳要在眾目睽睽下,被連人帶輪椅的扛進去,遊樂場的隊伍前、藝文展場的座位挑選,一句:「基於安全問題。」從此失去了許多參與的機會。一直以來都是別人在告訴著我,因為你的身體不方便走幾步路,因為你坐輪椅會影響逃生,我開始憎恨自己:「都是因為我癱瘓了。」
如果走不出去,無法參與這社會的任何事物,那麼生命將以最快速度枯萎,遠遠超越建立信心的時間。
兩年當中我幾乎如同廢了武功的武士,覺得人生到此已經算是完蛋了,沒有未來的生活只能苟延殘喘地活,一蹶不振剛好可以形容當時的狀態,還好拜網路所賜,我開始有了接觸房外世界的機會,躲在螢幕的後方,以一個偽非障礙者姿態,訴說這段痛苦的故事、與讀者進行鍵盤交談,直到一次契機,一躍從網路作家成為實體書作者,我正式踏出房門,重見天日,但那些環境上的問題,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很慶幸的是,在我認識了一些朋友之後,我發現「障礙」並不是來自於我身體的狀態,而是環境上的障礙,造成了我出門的諸多阻礙。就在這個時候,我才能推開被建築起的自卑感,勇敢地與這環境開始對話。
現在,這個專欄園地裡,想來談談我與這環境之間的關係,也許有些狀態會讓大家看了一陣錯愕「啊,原來障礙者是這麼想的!」或者你會感覺到不太舒服「我又不是那個意思。」但這都是身為障礙者內心最真實的感受,有時候不說,只是想體貼,或者是害怕說出口,無法接受真實狀況的人,會不再與障礙者和睦相處了,選擇說出口,更是想降低因不瞭解而產生的誤解,減少傷害與不必要的冤枉路,在台灣出生的大家,擁有理所當然的生活基本權利,我們更該去捍衛其他族群的生活基本權利,提升這環境的生活品質。
從來就沒有人想成為弱勢族群,弱勢,是被製造出來的,先放下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純粹來聽一位女性障礙者,談談生活當中所遇見的兩三事,所有的心事。
  |
 媽媽,才是一切的答案:化解與青春期女兒的情緒化衝突
媽媽,才是一切的答案:化解與青春期女兒的情緒化衝突大多數的媽媽都會面臨如此的兩難困境:若要當個最盡責的母親,妳得成為最完美的自己。然而,太常去做完美的母親,會讓妳人格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感到自己多餘並且被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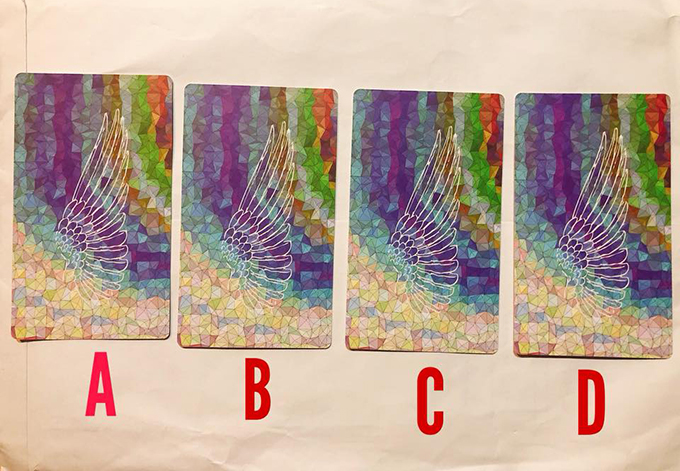 占卜測驗-在新環境讓天使陪伴你度過
占卜測驗-在新環境讓天使陪伴你度過暑假過完又是一個新學期的開始,相信很多朋友即將進入新的環境會感到特別緊張及焦慮。今天將邀請四位大天使到我們身邊,陪伴著我們一起迎接新的環境,現在就來看看大天使們分別要帶來什麼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