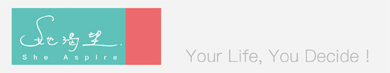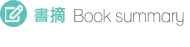《五天》你以為你愛過,痛過,經歷過,但你有賭上全部嗎?/ 寶瓶文化
![]()
摘自P40~P42
在緬因,我們習慣把一切藏在視線之外。
我獨占了海灘。現在是下午三點十八分。一個完美的十月天。天空湛藍,空氣中有些微顯露的寒氣,而陽光——此時威力已開始減弱——仍然閃亮。我的緬因。我一輩子都住在這裡。生在此,長在此,受教育在此,結婚也在此。直到今日的整整四十二年,我都靜定地守在同一個地方。這怎麼可能?我怎麼能允許自己固守一處?為什麼我認識的許多人也都這麼說服自己活在有限的視野中?
緬因。我常來這裡,就像我的避難所,此地總能以環繞我的自然之美讓我記得保有謙卑。然後是海。兩年前,我在一個讀書會中讀完了《白鯨記》,其中有位海軍退役的女性名叫克里斯朵.歐爾,她大聲表示不懂這些作家為何深受大海吸引,還愛把大海當成人生隱喻。當時我聽見自己回答:「或許是因為,當你在海邊時,人生感覺不再充滿限制,眼前彷彿有無限可能。」克里斯朵補充:「在所有可能中,最大的可能就是逃亡。」
那女人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嗎?每次我來這裡面對大西洋,心裡總想:那裡有個跟我身後完全不同的世界。當我面對海水,背向人生中的一切,就能活在此地之外的幻象中。但手機發出的「叮叮」聲瞬間把我帶回了現實。有人傳簡訊來。我馬上伸手在包包裡翻找手機,一定是我兒子小班傳來的。
小班十九歲,是緬因大學法明頓分校的大二生,主修視覺藝術——我丈夫丹恩對此有點抓狂。他們之間向來沒什麼共通點。畢竟我們都是由各自人生經歷所塑造的成品,是吧?丹恩從小在艾魯斯達克郡長大,童年窮困,父親是兼職木工,一天到晚都在喝酒,醉醺醺的他根本不知道「責任」兩字怎麼寫。他愛他的兒子,只是喝醉時總會痛罵他,也不覺得那有什麼大不了。成長過程中,丹恩對爸爸又愛又怕,總想成為父親自我定位的那種稱霸戶外活動的強悍男子。丹恩滴酒不沾,每當我想喝第二杯酒時,他總會斜睨著眼阻止我,顯然因為爸爸一喝酒就勃發的怒氣留下了不少創傷。他內心清楚,爸爸就是個軟弱、沒種的傢伙,跟所有霸凌者一樣,對他人殘酷不過為了掩飾對自己的厭惡。因此,我總是藉各種機會告訴丹恩,他比他父親好多了,因此,就算跟兒子的個性天差地遠,他也該把他內心溫和的那一面與兒子分享。當然,丹恩沒有以冷酷及敵意對待小班,但他仍只願付出表面的關心,並拒絕解釋自己為何總把兒子當陌生人。
就在最近,因為一幅在波特蘭美術館展出的拼貼畫,小班以備受關注的新秀藝術家身分上了《緬因今日報》。根據報導,那幅畫「將解構後的龍蝦籠轉化為『當代幽閉感的驚悚幻影』」(至少《波特蘭鳳凰報》的評論家是這麼說的)。丹恩看了後問我,小班有任何「精神上的困擾」嗎?我努力掩飾內心驚駭,反問:「你怎麼會這麼想?」
「哎呀,光看波特蘭那些自以為是的傢伙稱讚的那幅拼貼畫不就知道了?」
「人們對這幅作品產生回應,是因為它的議題性——而且還使用了具有緬因在地性特色的龍蝦籠作為……」
「在地性,」丹恩拉出一抹明確的冷笑。「你又開始用你那些花俏的詞彙了。」
「你何必傷人?」
「我只是表達意見。但你繼續講呀,我會閉嘴。這大概是我失業一年半的原因,當時……」
「除非你之前有所隱瞞,不然你並不是因為說了像剛剛那樣不得體的話而失業的。」
「所以我剛剛說的話不得體?不像我們『了不起』的兒子那麼『得體』?緬因的下一個畢卡索?」
自從失業之後,丹恩時不時就要展現出惡劣的一面。雖然他等一下就會針對這段話道歉(「我又來了,真不曉得你怎麼受得了我。」),但效果早已腐蝕人心。就算一個月只發作兩次,不過丹恩確實愈來愈封閉,針對自己被開除的事,他也不願合理地發洩怒氣,結果就是家中氣氛變得詭異。倒不是說我們的婚姻之前有多浪漫、熱情(我也沒有其他可比較的婚姻就是了),但以往固定發生的摩擦至少在合理範圍內,可是丹恩的失業彷彿在這段婚姻中打開了一道黑暗裂隙。隨著困守在家的時間愈長,他愈擔心再也無法回到職場,這道裂隙也隨之擴大。
我可以感覺到,丹恩因為兒子十九歲就在事業上得到認可而焦躁不安。他被選為波特蘭美術館的緬因年輕藝術家代表,是展覽中僅有的兩名大學生之一,而且還有名評論家認為他是值得關注的新秀……好啦,身為他的母親,我很驕傲,但你得承認這確實稱得上一項成就。小班是個心思細膩的年輕人,古怪得令人讚嘆,同時渴望父親的愛與認可,但丹恩就是看不清這點。根據各種跡象顯示,他暗自認為這名非我族類的奇怪男孩不是理想的兒子,因此無法接受他成功且備受讚譽的事實。我總是告訴自己,等丹恩找到一份好工作,一切都會好起來,但同時忍不住想:要是有什麼能立刻改變現狀的靈藥就好了。

* * * * * * * * * * * *
摘自P55~P62
我走回車上,插入鑰匙,發動引擎,開出停車場,轉眼大海已被拋在身後。我向左轉,沿著狹窄蜿蜒的小路繼續往左前進,時序已逼近陰冷殘酷的冬季,這條曲折的道路會帶領我經過那些空蕩蕩的夏季別墅,接著再次右轉,爬上一道兩旁住了半島居民的緩坡。除了少數藝術家和新世紀按摩師之外,此地大多居民在學校教書、賣保險、建造當地橋梁、從海軍退役、在巴斯的造船廠工作,或者正靠退休金或社會福利金過活。這些房子—— 大多需要重新粉刷一下(跟我的房子一樣)—— 很快就從視線中消失,眼前緊接著出現一片開闊原野,接著是向西回到城鎮的主要道路。之所以提起這一切,是因為自從我和丹恩十三年前搬來此處,每週至少得開車經過這裡三、四次;除了每年有兩週出外度假,緬因州的丹姆里斯柯塔(Damriscotta)就是我的人生重心。最近我才意識到:我沒有護照,距今最近的一次出國已是一九八九年,當時我在緬因大學就讀大三,拜託還沒成為丈夫的丹恩開車帶我到魁北克渡假。當時只要用美國駕照就能跨越加拿大邊界,而魁北克正舉行冬季嘉年華,到處都是雪,老城街道鋪滿鵝卵石,建築物裝飾成薑餅屋的樣子,而且每個人都說法文。我從未見過這麼魔幻、異國的場面。丹恩一開始因為不熟悉的語言和口音而有點緊張,最後也沉醉其中。雖然我們待了四天的旅館有點老舊,狹窄的雙人床只要我們做愛時就嘎嘎響個不停,但整體氣氛還是好浪漫—— 我確信就是在那兒懷上了小班。在我們發現要成為父母之前—— 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 丹恩說我們隨時能再來魁北克玩,以後也還要去巴黎、倫敦、里約熱內盧……
年輕人多天真,總相信人生結局尚未寫定,只要活著就有無限可能。直到你遇見足以扼殺所有可能性的轉折。
我就這樣在此地生根。我常想到這件事,但潛台詞並非針對丹恩的憤慨。無論婚姻出了什麼問題,我都不會把後來的生活發展怪罪於他,畢竟我也出手造就了這一切:是我決定要跟他結婚。現在我知道,我做決定的判斷力並不是那麼好。人生總是這樣嗎?明明只是倉促做下的決定,卻可能就此改變了一生?
我常聽到患者談及類似的懊悔經驗。老菸槍對於享受第一口菸的那天痛悔不已。極度肥胖的患者大聲質問自己為何無法停止進食衝動。另外還有那些真正傷懷的靈魂,他們深信體內隨機出現的腫瘤——和醫生提及的任何「生活風格」都沒有直接關聯——而是針對自己特定惡行、累積的罪孽,或無法在此珍貴一生中領受簡單快樂的(來自上帝或其他力量的)報應。
曾有段時間,聆聽人們因為對未知的恐懼與死亡威脅而冒出的人生告解,對我來說不過是例行工作。然而現在,這些掃描室告解開始以某種直接的方式令我不安,難道是因為被迫反思不停加速的時光軌跡?又是十月了,我已經四十二歲,卻還是搞不懂為何一年總能結束得那麼快。我爸— —他在水村的高中教微積分— — 數年前曾以非常優雅簡潔的話語為我解釋了這個謎團。當時我正提到人近中年的神祕之處:只要三個眨眼,一年就過去了。
「等你到了我這年紀……」他說。
「等我到了你這年紀?」(他當時七十二歲。)
「人永遠都很悲觀。不過我猜想你的工作也會造成這種結果。好吧,讓我換種方式講,如果你到了我這年紀……你會發現兩個眨眼就是一年。要是我活到,比如說,八十五歲吧,一年最多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其實只是簡單的數學公式——跟歐幾里德定律無關,而是收益遞減規律。還記得你四歲的時候嗎?一年感覺如此悠長而緩慢……」
「當然。我還記得每次過完聖誕節,都覺得下一次的聖誕節遙不可及。」
「就是這樣。但重點是:當時一年只是你人生的四分之一,但現在……」
「三十九分之一。」
「或者就我的例子而言,是七十二分之一。時間隨著年歲累積而縮水,至少感覺上是如此,而本質上,所有感受都是個人詮釋。經驗主義告訴我們,時間不可能延長或縮水,一天永遠是二十四小時,一週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改變的是我們對於光陰流逝的感知,以及作為一種有價之物,它如何變得更加珍貴。」
我的爸爸,他去年過世了。死前受阿茲海默症緩慢而殘酷的折磨,心智陷入五里霧中,但距今十二個月前,他的腦袋仍如此清晰;正如四年前,我母親因為無來由的胰臟癌過世之前,意識也是那般清晰。他們是大學中少見的那種聰慧伴侶,之後共同走完了一生,難道這正是古往今來不變的愛情故事原型?我清楚記得小時候—— 尤其在我的青春期—— 他們的關係一度降到冰點。我還記得爸爸不停找機會暗示,當他還是大學生,而且是緬因大學數學系的明星學生時,從沒想過未來會淪落在緬因最小的城市之一教微積分。但其實是爸爸顧及住在班戈的年邁父母,才在畢業後拒絕了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選擇留在緬因大學讀書,就為了怕逐漸年老的他們出什麼事。也因為如此,當無法在州內大學找到教職後,爸爸接下了水村的工作。
我的爸爸。
我的父母算不錯了。雖然過了幾年顯然緊張且沉默的日子—— 兩人之後不太提起這段時光—— 我仍擁有堪稱穩定的童年。他們各有事業,也有自己的興趣—— 爸爸在業餘的弦樂四重奏樂團擔任大提琴手,媽咪則是某種舊式針線活的專家。面對我時,他們總是不吝付出支持與愛,至於他們各自或兩人之間的苦痛或疑慮,則是從來都不讓我知道(直到我超過三十歲,必須每天面對家庭生活壓力時,才明白這種自制力多令人欽佩)。沒錯,爸爸應該在某間大學擔任首席教授,甚至早該出版以二進位數理論為主題的開創性著作。沒錯,媽咪應該有機會看遍世界—— 她曾說過那是她年輕時的夢想。我偶爾也會感覺到,她覺得自己太年輕就結婚,從沒機會好好認識自己丈夫以外的世界。然後,沒錯,在我出生後兩年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哀傷的事:我媽經歷了非常駭人的子宮外孕,不只失去了孩子,嚴重的併發症還使她被迫切除了子宮。一直到我懷了莎莉,以為出現併發症而大受驚嚇時(事後證明只是假警報),我才知道有這件事,也才知道為何自己是獨生女—— 我多年前曾問過她,但她只簡單解釋:「我們試過了,但沒再懷上。」直到目睹我也可能子宮外孕的夢魘,她才說出實話。我不禁好奇,為何她等這麼久才願意把真相託付予我?這場顛覆了她人生的慘劇想必始終縈繞不去呀。媽咪勢必看出我眼中的震驚,那是受了傷的震驚,因為我正努力了解她為何從未向我吐實,還有,爸爸—— 我以為我們之間毫無祕密—— 竟也和她共謀,對我隱瞞了家庭拼圖中如此重要的一片。但我的個性就是如此—— 是的,小班說得沒錯,我總想為親近的人解決問題—— 在知道事實之後,我從未吐露不停徘迴於體內的痛楚。我的個性就是這樣,總是想辦法合理化一切:他們一定是害怕對我產生不好的影響,(要是在我太小時告訴我)我可能會因為身為倖存者的罪惡感而受苦。但這一切還是讓我困擾,二十四歲才知道這個恐怖的故事……只是加劇了我內心的困惑。
丹恩的反應倒是直截了當,雖然我一開始覺得有點唐突,但只要多想一下,就能意識到那反應直指核心。他只是聳聳肩後說:「所以,現在你知道大家都有祕密了。」
一種冷淡的安慰。丹恩從不說那種黏膩的好聽話。外表看來我們是對運作良好的伴侶,有點錢,正準備承擔成為父母的責任。我們把一切都處理得很好,收入能支付生活,還買了棟房子,打算成為養育兩個小孩的雙薪家庭,但沒有認真尋求任何育兒相關的協助(除了偶爾拜託保母或婆婆幫忙)。我們會因為嬰兒半夜腹絞痛睡不好,但隔天還是能拿凌晨四點的暴躁相向來開玩笑。對於失去自由,我們當然沮喪,但儘管生活面對的全是孩子與經濟負擔,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那些年我們努力相處、避開許多潛在衝突、幫助彼此度過各種難關,而不需要玩「我為你做了這件事,現在你得為我做那件事」的遊戲。我們似乎是一對合得來的伴侶。
一對合得來的伴侶。聽起來非常合理、務實,完全缺乏激情……我們談的從來不是什麼世紀之戀,但上次做愛也不至於追溯至柯林頓總統任期。我們還有性生活,但早在丹恩失業並開始疏遠我之前,我們的性愛就已失去基本熱度,也少了彼此渴望的動力。還記得剛遇見他時,他吸引我的就是個性安穩、臨危不亂、有條理、負責任,不像之前我遇到的男人……
不,我不想繼續思考……他……現在的他……即使如此,老實說,我還是每天想著他,甚至比過去兩年被真相反覆打擊的時光還要……
別想了。
我的腳步早已停下。
別想了。
你失去了一些,也做了一些選擇。
我是不是在哪裡聽過類似的歌詞?我爸過七十歲生日的那個週末,曾懊悔地向我說了,「活著就是不停地與懊悔纏鬥。」或許是這個吧。
難道這就是存活的代價:不斷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失望,最後只能湊合著屈就眼前的生活?
別想了。
今早的場面足以讓我明白兩人如今的生活樣貌:鬧鐘一如往常地在六點響起,丹恩的手臂探了過來,我半夢半醒,很高興被擁抱,一邊感覺他正脫下我平日作為睡衣的長上衣;但他毫無愛撫意願,只是立刻騎上來,親吻我乾燥的嘴唇,迫切粗暴地進入我,沒過多久就發出了低沉呻吟,滾回床上,還翻身面向另一邊。我問他還好嗎?他握住我的手,但仍不願面對我。
「有什麼不對勁嗎?」我問。
「為什麼一定有什麼不對勁?」他連手都收回去了。
「你感覺……心神不寧。」
「你就是這樣看我的?心神不寧?」
「也不用生氣吧。」
「『你感覺心神不寧』,這不是在批評我嗎?」
「丹恩,拜託,你太誇張了……」
「你看吧!你看吧!」他下床跺步走向浴室。
「你說你不會批評我,但現在呢?難怪在你旁邊我永遠、永遠做什麼都不對,難怪我不能……」
他的臉突然垮了下來,開始斷斷續續地低聲啜泣——那哭聲之壓抑,幾乎像是要窒息。我立刻下床走向他,張開手臂,但他馬上避開我,走進浴室,用力甩上門。我還能聽見他在哭,但當我一邊敲門一邊說:「拜託,丹恩,讓我……」
丹恩打開水龍頭,水聲淹沒了我之後說的話。
讓我幫你。讓我接近你。讓我……
水不停流。我回到床上坐了許久,然後一直想、一直想。絕望的情緒如同我每天在可能患病的身體裡注射的化學染劑,透過血管流遍全身。
所以我也病了嗎?患上某種癌症?他因為失業患上「不快樂癌」,現在還全方位地轉移滲透到各處……
浴室裡的水還在流。我起身走到門邊,努力想分辨他是否還藉著水聲在哭,但只聽見潺潺不停的水聲。我看了一下手錶,早上六點十八分,除非莎莉因為剛剛的吼叫聲醒來,不然我該去叫她了。莎莉通常不會對這種場面感到擔憂,比如幾星期前,她目睹丹恩對我發火,也只是故作俏皮地說了:「很高興成長於一個如此快樂的家庭。」
擊中要害。
我們曾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嗎?我遇過任何真正快樂的家庭嗎?
![]()
作者簡介-道格拉斯・甘迺迪(Douglas Kennedy)
1955年出生於紐約曼哈頓。其作品《如果那天我沒死》和《找死頭路》兩部既長銷又暢銷的小說,皆在國際書市獲得極高評價。他的小說至今已被譯成22國語言版本,首部小說《死亡之心》已拍成電影《Welcome to Woop Woop》,《如果那天我沒死》也已於2010年在法國搬上大銀幕。甘迺迪尚有《A Special relationship》、《State of the Union》,以及《第五區的女人》等作,後者亦翻拍為電影,由伊森‧霍克與克莉絲汀‧史考特‧湯馬斯主演。他因文學上的成就,於二〇〇七年榮獲「法國藝術暨文學騎士勳章」,二〇〇九年獲頒法國「費加洛報」文學大獎。
譯者簡介-葉佳怡
木柵人,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被偷走的人生》、《死亡之心》、《返校日》、《缺頁的日記》、《被抱走的女兒》、《為什麼是馬勒?:史上擁有最多狂熱樂迷的音樂家》等十數種。
  |
 Margaret 專欄|妳萬分忙碌,卻更加專注—善用零碎時間解決待辦事項3撇步!
Margaret 專欄|妳萬分忙碌,卻更加專注—善用零碎時間解決待辦事項3撇步!當媽之後,時間被切割成零碎。想要照顧寶寶,也不願放棄事業,那是自我實現,或為薪資以換取日庶所需不得停止勞動;於是在洗滌、晾曬、哄抱、餵食之間,我們騰出雙手,嘗試空出腦袋的一方一隅,
 Margaret 專欄|第「零」個母親節
Margaret 專欄|第「零」個母親節從無到有、從零起頭,人的歲數從「零」開始計,在這邁入孕期的最後階段,當我挑選著初生嬰的小衣服、奶瓶奶嘴、尿布包巾,感受「零」所開啟的力量—尚未謀面卻已然孕育了母性。
 Irene專欄|在茫茫個人品牌的大海中,我到底要怎麼找到利基市場?
Irene專欄|在茫茫個人品牌的大海中,我到底要怎麼找到利基市場?你正在疑惑你應不應該要利基市場(縫隙市場)?你擔心你一選擇方向,就會損失你現在想要支持你的人?為什麼要有利基市場?利基市場真的有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