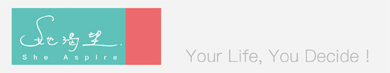姐妹/ Klang
住在家樓下,一起上學,下了課再一起搭車回家,有時期同班,有時一起談戀愛,更多時候一起煩惱數學怎麼解,一算,也過了一個十年。
生命中這麼多時刻重疊,是姐妹。
考完試各自上大學,離開了原自的家,展開另一種生活,也許,另一個生活圈,也圈成另一群的姐妹。但是那些重要日子、長假開始,彼此一定會記著約吃飯,短遊幾天,或是一下午的咖啡拉拉雜雜更新了一堆;有的時候不說,她用猜也能猜出妳心裡的意思,因為妳一個眼神,或那麼經典慣性的撇了嘴。分了幾次手,流轉幾個國家,到了各自開始求職就業的時刻了。
「你好嗎?」午餐休息,吃完自助餐手中拿著熱咖啡,面對她的問題,實在想了一下。昨天還在交不出作業、被當數學,今天打卡上下班,看訂單貨進貨出,而明天,我們會在哪裡呢?
夏天創作排練時一次晚餐時間,我問劇組中的女孩,再過五年,妳想過生活會是甚麼樣子嗎?她說,也許開了自己的咖啡店,結了婚,可以邊顧店邊顧小孩。
她的話像長鏡頭在我腦海展開,很美但是有點遠。
此刻的我想起來,好像湊起來了。生命的階段不停更迭,我們都在路上。
在姐妹的眼中,客觀的照見自己一路走來的模樣,也許鼻青臉腫,也許還有當初的熱誠衝動
此刻我們走到這裡,也許會走到劇組女孩那一步
也許,還有,或者更多可能
不論風景為何了,事情永遠在變,但沿途有姐妹陪伴,看生活看工作看自己,心裡已是滿滿慶幸。
「親愛的,有妳我很好。」
  |
 她渴望-2022年系列活動回顧
她渴望-2022年系列活動回顧回顧2022年,我們共舉辦了104場次女性專屬活動,包含了創業類3場次、心靈類8場次、生命經驗與讀書分享4場次、運動類89場次,很感謝因認同公益付出理念願意在她渴望開課的老師,以及參與活動的姐妹們
 張德芬:你會選擇什麼樣的伴侶,寫在你的父母關係裡
張德芬:你會選擇什麼樣的伴侶,寫在你的父母關係裡你和媽媽非常親密,我完全能夠看到日後你和女友、老婆互動的方式,會不由自主地「延續」我和你的關係。很多心理學家說過,我們每個人都會不自覺地重複自己童年的經驗,尤其是和父母之間的互動方式。
↑